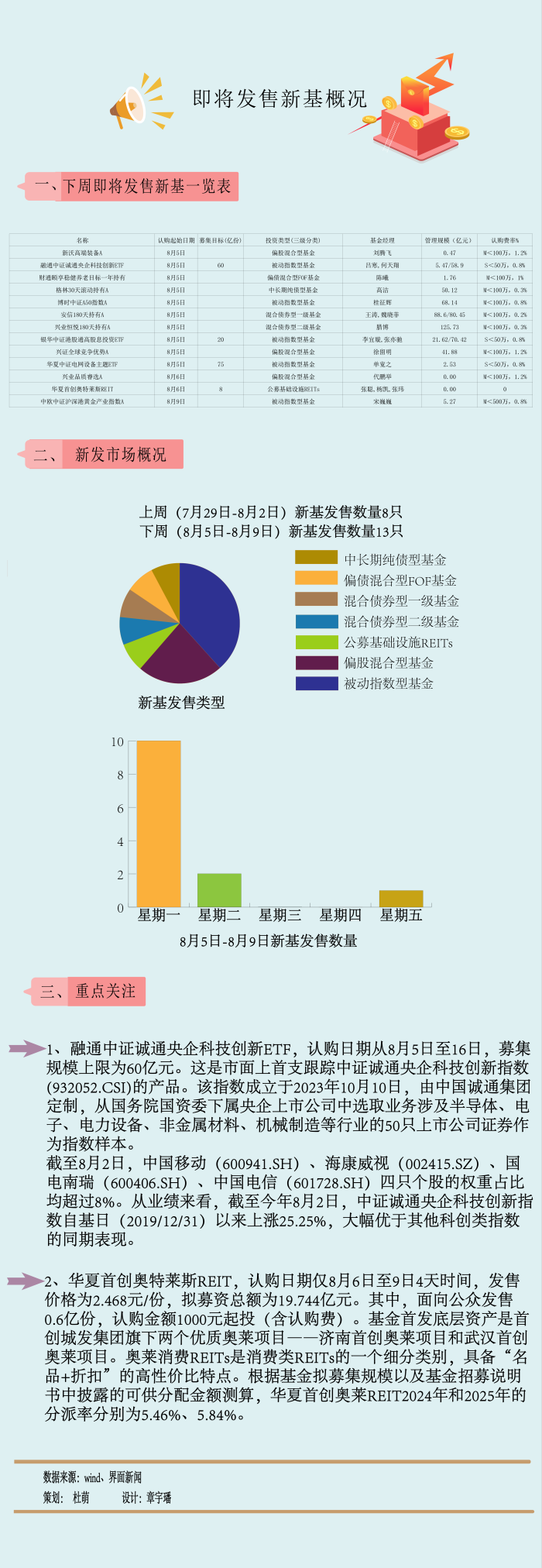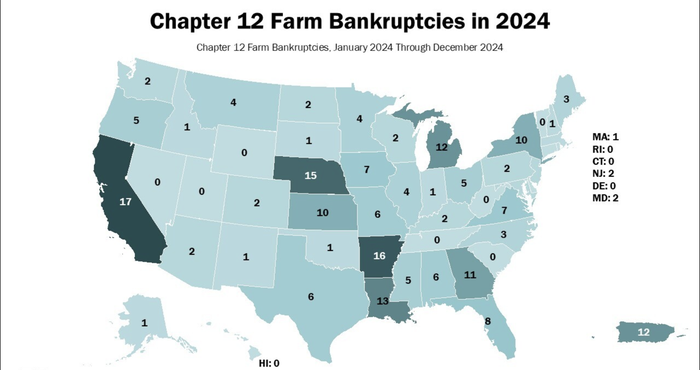美妆生意人捱“寒冬”:价格卷无可卷,只能拼其它
界面新闻记者|朱永玲
界面新闻编辑|娄勤俭
打开手机里的外卖App,像订餐一样买化妆品,然后等着骑手在几分钟内送货上门。这种被称为“美妆外卖”的实时零售业态,正在成为美妆零售创业者新的掘金赛道。
美妆外卖店连锁品牌美有美创始人刘波告诉界面新闻,2022年秋,他在杭州开了美有美第一家直营店。一年后,这家店的月销量从1000增加到5000。同时,美优美妆通过加盟模式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铺开。不到两年的时间,门店数量已经达到260多家。
刘波回忆说,当他开第一家美容外卖店时,附近只有一个同事。到了2023年、2024年,同事的数量明显一年比一年多。
刘波从事新零售行业多年。从2022年年中开始,他就经常听业内的朋友说,美妆新零售走在前列。当时各大电商平台已经开始抢本地生活业务,趋势之一就是在餐饮外卖、团购等业务之外,开辟更多品类的即时零售。
美妆外卖并不是全新的。早在2022年,美团、饿了么等平台就开始和一些类似屈臣氏、丝芙兰的美妆品牌店、美妆集合店合作。2020年疫情爆发是一个契机。

在刘波看来,美妆外卖店和那些入驻外卖平台的美妆品牌店、集合店并没有直接的竞争关系。后者多为中高端名品,而美妆外卖店,尤其是美柚美妆,优势在于覆盖更实惠的价格区间,24小时营业,这对于满足应急需求尤为重要,而应急是即时零售的常见场景。
不过,刘波认为,美妆外卖的客户群不止于此,还包括那些“拍照方便快捷的年轻人”。“现在大城市很多人都有这种消费习惯。吃喝玩乐,买生活必需品,一个平台一站式解决。”
刘波相信人们会像网购一样逐渐接受这种新的购物方式。“我们看好这个项目的稳定性,这个层次的消费者会一直存在。”
虽然美妆新零售的利润率远低于他之前做过的鲜花、蛋糕、水果等高利润品类——后者的利润可高达200%甚至300%,但美妆外卖的同质化和激烈竞争远低于后者,是“相对稳定”的。
对于创业者来说,开一家美妆外卖店的吸引力在于相对较低的启动成本。
美妆外卖店相对于开美妆店或者电商C店(个人店)来说,在租金、人力、流量上可以节省很多钱。据刘波介绍,美柚美妆单店加盟费用在10万元至15万元左右,多为情侣。当然,如果自己开店,只卖低价的样品商品,选址在非一线城市,SKU只满足平台最低要求,成本是可以降低的。在山东济南经营一家美妆外卖店的创业者告诉界面新闻,他的启动成本没有超过5万元。
商品是开店成本的大头。作为美妆外卖店这样的非官方零售渠道,其供应链一般分为国产美妆品和进口美妆品。国内美妆的供应链比较单一。比如一些大的零售商可以直接从品牌进货,省去了中间商的环节。进口美妆产品的供应链更长,货源往往是国内外的品牌专柜、免税店或品牌。因为订单量大,涉及跨国物流和报关手续,所以出现了一个专门从事采购和仓储物流的大型供应商。
美妆供应链服务商中汇融信负责人陈小虎告诉界面新闻,大型供应商主要依靠批量采购、免税、汇率价差等方式降低进货成本。以中汇融信为例,其采购来源包括韩国、泰国等亚洲国家的免税店,以及欧洲的百货专柜,还有一部分是品牌提供的一级货源。
有些供应商有自己的优势品类,可以拿到更低的价格,但总体来说,这个环节的利润基本稳定在空之间。“市场很透明,下游客户也知道我们的采购价格。我们的角色只能赚这么多利润。”据陈小虎介绍,通常大型供应商可以拿走最终销售利润的3%到6%,而下游零售商的利润点大概是10%到15%。
虽然看起来是红海中的一片蓝海,但是美妆外卖店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整个美妆市场天气变冷的影响。刘波发现,那些单价几十万元的名品越来越难卖了。“去年‘520’一家店卖了七八十支大牌口红,跟玩似的。今年可能只卖十几二十个。取而代之的是一套100多元的盒子和一条几十块钱的925银针项链。”
美妆市场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在疫情过后迎来强劲复苏。
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,2024年1-5月,我国化妆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.4%,远低于2019年同期11.3%的增幅。整个2023年,中国化妆品零售总额2022年低基数增长5.1%,较2021年增长2.9%;疫情发生前,2015-2019年,我国化妆品零售总额年均复合增长率为9.9%。
但考虑到美妆外卖市场还是空小白,美柚美妆还是有扩张计划的,只是把目光从竞争激烈的一二线城市转向了需求相对较小、运营成本较低的下沉市场。“我们的下一个计划是在三线以下城市扩张,比如浙江的丽水和衢州。在这个地方,加盟商一个月能做三五百单,自己完成配送,在房租等成本不高的情况下,一个月能赚五千、八千就很不错了。”刘波说。
从外卖仓库转到美容店,是直接拒绝的选择。一个原因是实体店生意可能不好做,其投入成本会高很多。“我们项目的单店启动费用基本都是10到20万封顶,再高就不那么好(加盟)了。”刘波说。
总有人能在不景气的环境中找到新的机会,但与这些热情的新玩家相比,大多数美妆供应商和零售商的常态是在谨慎的同时,面对业务的萎缩,努力寻找出路。
在重庆经营一家区域性美妆连锁品牌“盈彩堂”的陶告诉界面新闻,盈彩堂美妆集合店自2006年成立以来,一直是完全自营,2017年左右的高峰期开了40多家店,但随后线上渠道的发展和疫情相继冲击实体零售,将这一数字减少到今天的11家。
当地同行的情况也不乐观。在陶观察的重庆市场,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妆店比疫情前倒下了,包括大型美妆连锁品牌。“我们不是被对方杀死的,而是被其他渠道和整个环境杀死的。”陶秋成说道。
因为门店密度远不如以前,“一个购物中心可能连两三家(美妆集合)店都没有”。美妆店的竞争不再来自线下同行。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线下客流的下降和线上价格战的冲击。这迫使商家试图降低价格和改善服务,以留住那些会光顾实体店的顾客。陶观察到,疫情过后,消费分层趋势明显,线下购买美容化妆品的往往是对品质有要求、更有消费能力的人。
英才堂因此调整了产品结构,增加了单价较高的进口产品比例。目前店内主要产品价格在300元左右。同时,他们也会关注线上渠道的折扣和价格,对门店的定价做出相应的调整。比如618电商大促期间,英才堂也会单独在店内做一些优惠和购买活动。
【/h/]但是由于第三方美妆供应链的质量和价格往往是直接挂钩的——太便宜很可能是假货,英才堂不敢把成本削减到极致,成本下限基本就是终点。为了避免卷入恶性价格战,英才堂在选择产品尤其是主打产品时,会优先选择那些市场价格保障较好、价格体系稳定的品牌。
服务和体验也是英才堂强化的区别于电商商家的优势。陶告诉界面新闻,蔡颖唐门店已经从过去单纯的门店,变成了一个可以给顾客带来更多“情感价值”的休闲体验场景,比如推出一个轻美容的服务,在维护老客户上多下功夫。“同款产品的网上价格总会比我们的低。我们要做的是如何为客户提供其他价值。”
在价格超出范围后,在最基本的商品交易之外提供更多的软附加值,是提升竞争力的常用策略。
上游美妆供应商也是如此。中汇融信的负责人陈小虎告诉界面新闻,现在美妆供应商同质化严重。除了价格差距,很难形成产品类型的差异,这主要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的。“一个美妆品牌卖的好的产品可能就那么几个。卖得好的永远会卖得好,卖得不好的也不愿意采纳。所以只能在服务和品控上下功夫。”
美妆产品是假货的重灾区。所谓的服务和品控,很大一部分是指正品保障,比如从免税店进货到仓库,这里面没人碰过货。
此外,随着市场信息变得透明,更多同行的涌入也使得中汇融信转向发展纯货以外的其他业务。自2018年初成立以来,中汇融信从最早的采购业务发展到报关、货代、保税仓储等系统的供应链服务,后者成为中汇融信的主营业务。
这些资源一度帮助中汇融信在疫情期间赢得了比前后更多的订单。因为当时货物流通受限,货代资源较好的供应商竞争力凸显。
但是疫情过后,下游零售端的寒意也来了。陈小虎告诉界面新闻,中汇融信在疫情后的表现“与疫情那些年完全无法相比”。
除了提升服务质量,发展配套业务,中汇融信还转向海外(海外)市场和C端零售寻找增量。
“在疫情爆发之前,我们试图将货物出口到中国大陆、台湾省和马来西亚的客户,今年我们也将目标锁定在中东国家的香水市场。”据陈小虎介绍,以马国为例,人均收入水平略高于中国,美妆零售商在采购时不会过度压低价格,比国内生意好。
此外,和很多同行一样,中汇融信也开始利用自身的供应链资源开展C端零售业务。小程序等线上私有域是首选,因为它可以不受平台规则约束,避免“随平台滚”。
和美柚美妆一样,中汇融信基本不考虑线下门店。因为从中汇融信与实体店客户合作的经验来看,规模稍大的美妆连锁店账期长,资金周转慢,与美妆零售的低利润率不匹配;对商品的要求也高,“一点点刮不到”,也会变相提高运营成本。
目前仍在守着美妆店的陶告诉界面新闻,英才堂也在网上寻找新的增长点。“就目前的情况来看,这个市场的容量会越来越小,如何拓展渠道,如何与线上融合,肯定会做。”
而线下,陶秋成预测,2024年英才堂最多新增一两家门店。开一家新店的投资是60到70万元。情况理想的话,大概三年就能回本,反之亦然。但是走一步看一步总比原地踏步好。
“最悲观的时候(2023年)已经过去了,现在已经适应了。”陶认为,虽然美妆市场或者至少是重庆市场依然冷淡,但已经进入稳定期,或许五年内不会有太大变化。
目前,熬过寒冬才是最重要的。